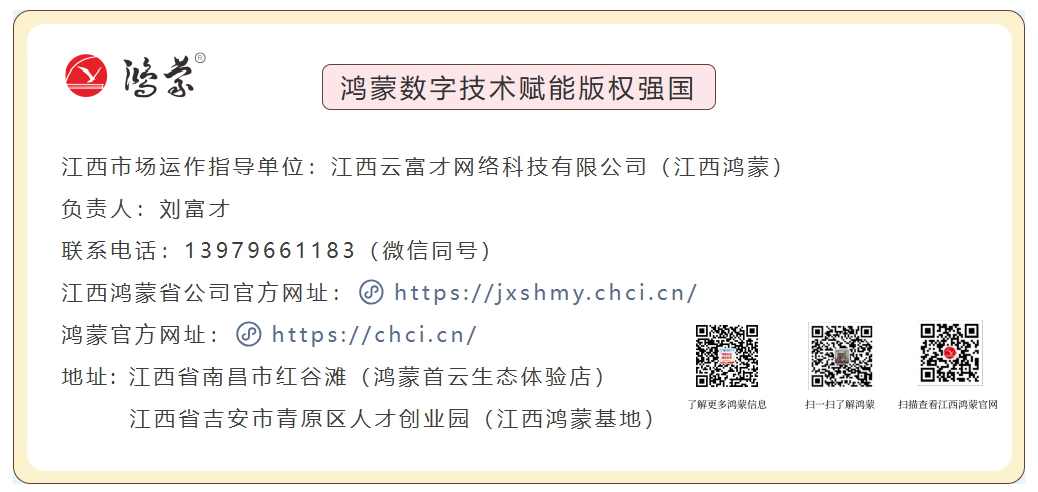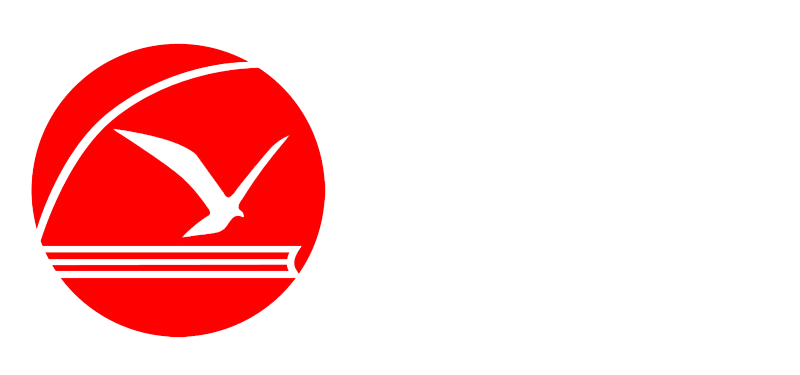相 关 分 类
当前页面: > 企业资讯 >
数据知识产权,企业真正期待它什么?
发布者: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今年要加快完善数据基础制度,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
企业的数据制度的核心诉求:司法推定力,而非一纸证书,投入巨额成本构建的高质量数据集合,在司法weiquan时却难以自证“数据是自己的”。
一、数据基础制度
2023年发布的《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数据二十条”)首次系统提出数据基础制度框架,明确将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列为四大支柱。作为配套政策,各地政府工作报告持续强调“深化数据基础制度改革”,其核心目标直指两大矛盾:
数据资源的海量沉淀与开发利用低效之间的矛盾;
数据要素的市场价值与权益保护缺失之间的矛盾。
在此背景下,数据知识产权制度具有前瞻作用,通过打通“数据资源→数据资产→数据资本”的数据要素市场的转化通道。然而,现有数据知识产权制度尚未实现这一目标,其根本原因作者认为在于对“数据知识产权”的功能定位存在认知偏差。
作者在之前的文章中,就分析过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公共数据流通机制的建设正逐步完善。然而,与之相对应的市场主体数据集合的权益保护制度尚未同步跟进,形成了数据治理体系中的关键缺口。这不仅影响了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深化,也阻碍了数据要素价值化的实现。
上一篇文章分析了,数据知识产权: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平台上线后,何去何从?国家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平台上线后,数据集合权益保护缺失,影响数据要素市场化进程。
作者认为数据知识产权登记制度未能真正触及数据价值的核心:
1、登记证书应成为司法裁判中的“权利推定依据”,而非需要二次举证的普通书证;
2、审查需验证劳动投入与规则体系,而非止步于算法规则描述与格式合规;
3、样例数据+数据处理规则锚定动态权益可验证,而非静态样例数据的形式化存证。
二、数据基础制度改革的现状
数据产权与数据知识产权登记是目前国家数据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分别推的工作,作者在数据知识产权: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平台上线后,何去何从?指出了数据登记证书复杂,后面作者将专门论述目前数据证书复杂,在数据流通的制度中,政策落地过程中滋生出以"证书经济"为核心的投机产业链这一问题。
现行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主要依托于“数据资源持有权—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的分置架构,通过标准化材料清单确认企业在特定时点上的数据控制权。
目前已经上线了国家公共数据资源登记平台,反而数据知识产权依然还在试点中目标摇摆,虽然国家数据知识产权登记管理平台悄无声息的上线了,但是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数据知识产权定义,更别说数据知识产权的审查标准了。
作者认为,目前不论是数据产权还是数据知识产权的登记,在材料准备上均试图通过一份“登记证书”来对数据权属或者权益进行界定,忽视了数据集合在生成、处理和演变过程中的内在逻辑和动态关系。
具体来说,现行的数据产权登记往往侧重于“谁持有数据资源”,而数据知识产权登记则强调算法规则和存证公证。在试点中各省市实质并非是作者在其他文章中强调的数据知识产权对数据集合的权益保护。
但无论哪一种登记,都未能有效披露数据生成的处理规则及其动态演进路径,从而无法在司法实践中为数据集合权利提供有限的排他性证明。在下一篇文章中专门论述这个问题。
三、数据企业对数据知识产权的期待
上周在北京,将我的一些想法和专家做了充分沟通,回来前,见了一家知名数据企业的负责人,我详细介绍了我对数据知识产权制度设立的理解,他非常认可,我个人认为他对数据行业是执着的热爱,对数据知识产权的权益保护的需求,才是数据企业真正的需求,并非数据流通和利用。有真正的数据企业的数据侵权诉讼成功案例。但是当探讨数据企业的weiquan的时候,我觉得数据知识产权制度确实还有很多细节有待改进。也让我深入了解了数据企业对数据知识产权的期待。
数据企业真正关心的并非仅仅获得一纸静态证书,而是期望借助数据知识产权登记制度实现以下三个目标:
第一个目标,登记后在先性推定
当企业获得数据知识产权登记后,期待司法机关可以直接采信数据知识产权登记的内容,从而认定企业对特定数据集合拥有数据权益,而不是在企业需要侵权诉讼的时候,让其陷入无限的自证。
第二个目标,数据集合动态权益权益边界锁定
数据集合在实际应用中,数据集合的字段关系、数据更新、处理规则,应用场景等均处于不断演变之中。先不说现有数据知识产权登记中一直强调的算法规则简要说明会导致数据权益模式,仅以单一时点的数据样本(样例数据)作为证明,将难以涵盖数据整个生命周期内的动态变化,数据权益边界是模糊、侵权举证困难,因此企业希望能通过数据知识产权登记的形式,锁定数据集合的动态权益边界,降低侵权举证接线。
第三个目标,简化数据侵权举证
数据企业希望利用快照比对、历史版本数据及字段关系匹配等技术手段,可以迅速判断数据集合是否被非法复制或篡改。这一点非常重要 ,这也是数据企业特别期待的数据知识产权证书的功能,企业所需要的,不是停留在纸面上的资产化概念,而是能够切实保护其数据权益、推动其市场化运作的机制,真正让数据创造的价值得以释放和转化,带来经济上的可持续收益。
但当前数据知识产权登记制度并未对数据历史版本和字段关联关系做出强制性要求,使得数据知识产权证书和举证难度之间关系并不充足。
作者在之前的文章中,就阐述过,目前数据知识产权试点中,数据知识产权的价值似乎仅限于“纸面效应”上的公信力,而没有充分转化为企业实际的市场收益,不能只存在于新闻宣传中,这个和最新一篇文章下面评论,数据知识产权的形式审查对数据确权根本没有任何帮助,目前各地在推的更多是个噱头。有同感,数据知识产权登记应是企业追求的数据权益保护。
作者认为,数据知识产权如果没有明确的权益边界和更为细致的制度设计,数据知识产权就可能沦为一个形式化的过程,企业所获得的“保护”不过是一张空洞的纸,无法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无法帮助企业简化数据侵权举证责任。
四、写到最后
在数据基础制度建设的国家战略框架下,数据知识产权正从理论构想走向实践落地,但作者认为核心的问题就是要解决企业的期待,
投入巨额成本构建的高质量数据集合,登记了数据知识产权证书,在司法weiquan时无需自证“数据是自己的”。
《数据二十条》提出的“数据红利全民共享”愿景,唯有数据知识产权制度设计者正视企业的核心诉求——要司法推定力,不要形式证书;要规则保护,不要算法披露;要动态权益可验证,不要静态形式化存证——才能真正落地。
政府报告对数据基础制度的聚焦,绝非简单的政策宣示,而是中国争夺数据规则制定权的战略宣言。在全球数据博弈日趋激烈的当下,数据知识产权制度已超越单纯的法律工具范畴,成为国家数字竞争力的核心指标。
数据知识产权制度改革更应关注——数据权益保护模糊抑制流通、规则缺失阻碍复用、保护不足压制供给和创新。只有这样,才能推动数据要素市场的健康发展,实现数据红利的全民共享,才能在数字经济全球竞争中占据制高点。
来源:数字知产